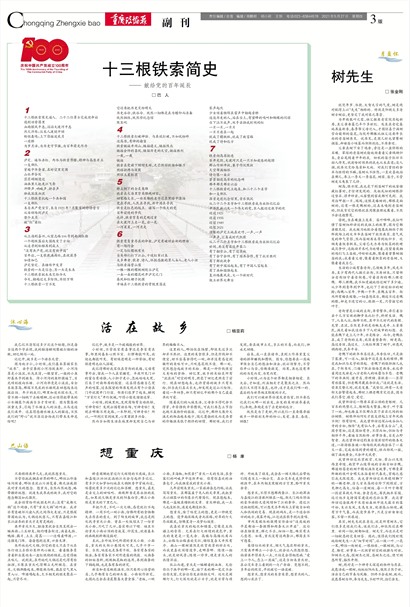树先生
就凭年岁、体貌、大智无言的气度,树是绝对配得上以“先生”相称的。特别是仰视太多老树古树后,更坚定了我对其之尊崇。
为开枝散叶之需,祖父搬离老家院另起新居,至父亲垂暮已半个多世纪。及至在老宅基地再盖新房,春季帮父母迁入,才因惊喜于满树雪白馥郁的梨花,与院外那株比祖父还要年长些的老梨树再见。说再见,是因儿时也曾攀树摘梨,却嫌梨小味寡而渐渐疏远,不再亲近。
父亲在树下安了鸡舍,旁边是一盘停转的石碾。翠绿的老梨树欢愉地俯看着父亲蹒跚归来,身后尾随着中年的我。初秋的梨子依旧不招人待见,就连啥时候熟的我也从未在意;没人摘,就再次交给鸟雀和大地。对我们曾经的舍弃与继续的不睬,梨树从不怪怨,一直欢喜地站在那儿,奉上一季又一季梨花、树荫、梨子,不管树皮又龟裂了几许。
树高,根亦深,我也是下到梨树下的地窖储藏红薯时,才惊讶发现的。或粗或细的树根挤过坚石、撑开砂岩,从窖壁到窖底都可见到。我用指甲抠一片,闻闻,这根是椿树的,那根是柏树的,还有一根是槐树的,还真未嗅到老梨树的,但我肯定它的根就在周围盘踞延展着,不然不会这般繁茂。
傍晚,坐在碾盘上发呆。梨叶哗哗,我似听懂了梨树细碎讲述的我祖上的故事,因为它都亲眼见过。我也极力地配合着想象我牺牲于朝鲜战场上的大爷爷在梨树下毅然离家、意气风发的帅气背影,然而梨树再未等到他归乡。炊烟夹着饭香飘来,父母已无力再为饭菜的软硬咸淡争吵,边拖动牙床吃力地嚼着,边望着夜栖的鸡们飞上梨枝,呼啦啦乱颤,像看着曾攀树摘梨的我;我看着父母,像看着飘零的老梨树,又像看着我自己。
生活的小城有条老街,已颓败多年,风光不再,至少有两代人搬迁出街,不再回来,只留部分老街坊守着老街巷,守着沿街的那三棵老槐。那三棵槐,我不知虔诚地经过树下多少遍,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也记下了新近标示的树龄:西槐八百年、中槐一千年、东槐五百年。街内所有婚丧嫁娶,一切喜怒哀乐,都逃不过老槐的眼,却走不进它的心,微微一笑,只管摇它的叶子。
老街曾是小城的主街,异常繁华,牵引着全县十几万百姓的脚步来此打卡,料理生活。槐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时代的英模、先贤、名流,当然更多的是些贩夫走卒、土著居民,满足着如我这些乡下人对城市的幻想。我能在槐下走上几十年,亦是缘分。而今,老槐依在,成了老街的主角,庇荫着整条街。树更高,高过房顶,高过天。三块红布围了树干,祈愿风调雨顺,民阜平安。
老槐下的新华书店还在,书香依旧,只是换了装潢,可一迈入,脑海中还是原来的模样,那是我知识与文学的源起。老槐下的烧饼摊儿也在,于街角处、门楼下飘出缕缕芝麻香,永远牵着周边及游走八方老街人的味蕾与乡愁。老槐下的书画院、镶牙店、修理铺、蛋糕房……显得有些落寞,但老槐用葳蕤告诉我:“这就是生活,荣衰交替之间,就是发展。”我坚信,终有一天老街又会繁荣起来,那时三棵老槐肯定还在,因为我们尊它、敬它、爱它。
我曾拜访过一隋唐石窟山顶的老栎树。几百米的绝壁之上,栎树高大繁盛,栎子、叶子落了一地,却也掩盖不住那凸显于岩石之间的粗壮树根。树根伸向何处才能支撑起上百年风雨不倒?惟有惊叹。我也曾拜访过深山峡谷仙人寺的古松,相传“先有仙人寺,后有五台山”,是因寺有松,还是因松有寺,不得而知,但松与寺相伴千年,看遍自然轮转、世事沧桑,自是山野智者。我还曾拜访过钓鱼台国宾馆外的银杏大道,一排排银杏被一场场秋风秋雨涂抹了一层又一层,完成由绿到黄的嬗变,继而劲风一摇,铺了满地黄金,只余冲天风骨。
我曾拜访过北京故宫、天坛、景山以及陕西皇帝陵、南京中山陵等地的古柏古松古槐,那遒劲苍老的树干镌刻满历史故事,可那青翠鲜嫩的枝叶分明又沐浴着时代春光,穿越之感引我无限遐思。我也曾拜访过水库堤坝脚下的一株老柳,沿几百米高的台阶下到跟前,方见柳之高大,似每一道树纹、每一片叶子都有一段前辈战天斗地、舍身忘死,居民抛弃家园、远迁他乡支持国家建设的悲壮往事。我还曾拜访过海拔两千米原始森林中遮天蔽日的落叶松,生云生风,生鸟生虫,宛若高山秘境,藏有万千气象,而我漫步其中,只是尘世匆匆过客,不留一丝痕迹。
其实,树先生就在身边,就是所有树木,它们很多是迎我们来,送我们去,却依然还在那里。世间一切,树都知道。树无言,而这正是对一切疑惑的完美回答。因此,值得我们随时随地给树先生一点“细节时间”,让一枝一叶、一花一果,哪怕一块树皮、一根枯枝、一眼树洞,与心灵、触觉、世事来一次洞穿时空的碰撞与对话,仰树木之高,探树木之深,感树木之远,便可洞悉所有,豁然开朗。
树,绝对是一个神奇又深邃的物种与存在。我愿活成一棵树,向地向阳而生,傲然孑然于世,活出自己的节奏与风格。但终不会成树,故而,我愿尊树为师,奉为先生,不时叩问,指引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