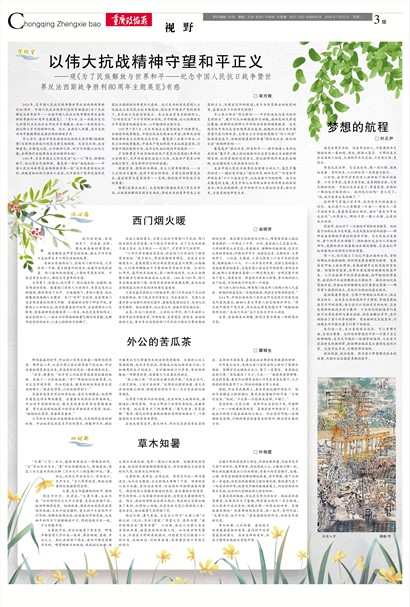草木知暑
“大暑”二字一出口,唇齿间便滚过一阵燥热的风。“大”字如烈日当头,“暑”字似蒸腾的地气,两相叠加,便是三伏天最炽烈的注脚。《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古人寥寥数笔,便把这酷暑的刻度描摹得分明。
大暑,是太阳最慷慨的时节,慷慨到近乎炽烈。农谚说:“大暑不暑,五谷不鼓。”此时的阳光已无半点含蓄,直直地泼洒下来,把田野晒得发烫。稻穗低垂,灌浆的谷粒在热浪里悄然饱满;玉米秆挺直腰杆,宽大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吞咽光热;就连最耐旱的芝麻,也在晌午的烈日下微微蜷起叶子,待到傍晚凉风一起,才又舒展开来。
大暑的午后,村庄如被置于蒸笼里。蝉鸣声稠密得几乎织成一张网,罩在树梢、屋檐、井台之上。狗趴在树荫下喘息,连吠叫都显得懒洋洋的。唯有蜻蜓不知疲倦,低低掠过池塘,翅尖偶尔点破水面,荡开一圈细小的涟漪。池塘里的荷花正盛,粉白的花瓣被晒得微微卷边,却仍倔强地立在滚烫的水汽里,似要与太阳较劲。
大暑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常常是午后一阵闷雷滚过,乌云还未聚拢,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田里的农人来不及躲,索性站在雨里,任由雨水冲刷掉满身的暑气。雨后的泥土蒸腾出潮湿的热浪,混合着稻禾的清香、野艾的苦味,以及荷塘浮动的湿润,这便是大暑独有的气息。偶尔,雨后的傍晚会出现火烧云,西边的天空犹如被泼了朱砂,红得惊心动魄,而东边的月亮已悄悄爬上来,苍白清淡,恰似被暑气蒸得褪了色。
雨过天晴,暑气更盛,正是古人所言“大暑三候”应验之时。《礼记·月令》有载:“季夏之月,腐草为萤。”最妙的便是这“腐草为萤”。小时候,我总以为萤火虫是星星的碎屑,被夏夜的风吹落人间。如今城里难见萤火虫,但若在乡野的夜晚静坐,仍能看见它们提着小小的灯笼,在稻田边、竹林里游荡,宛若暑热里不肯熄灭的诗句。
这般乡野的浪漫虽已难觅,但若细察街巷,仍能寻见节气留下的印记:菜市场里,西瓜堆成小山,小贩的刀锋一划,鲜红的瓜瓤便裂出沁凉的甜香;老巷口的凉茶铺子,乌梅、山楂、甘草在铜锅里咕嘟咕嘟地熬着,苦中带酸,喝下去却是一身通透;冷饮店的玻璃柜上凝结着水珠,像给暑气盖了一枚清凉的印章;就连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阳光折射出的刺目光斑,也如同从前晒谷场上的金灿灿。
大暑是热的极致,却也是生命力的狂欢。稻谷在热浪里灌浆,瓜果在烈日下蓄糖,蝉在枝头耗尽一生去歌唱,而人则在汗流浃背时,咂摸出那一丝苦后的回甘。是谁说暑热难耐?你看那田间的老农,抹一把汗,笑呵呵道:“大暑不热,谷子不结。”原来最酷烈的阳光,恰恰是丰收的伏笔。
草木知暑,人亦知暑。最深的炎热里藏着最甜的浆果,最闷的午后孕育最亮的萤火。原来生命的美妙,就在于懂得在极致处寻找平衡。